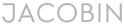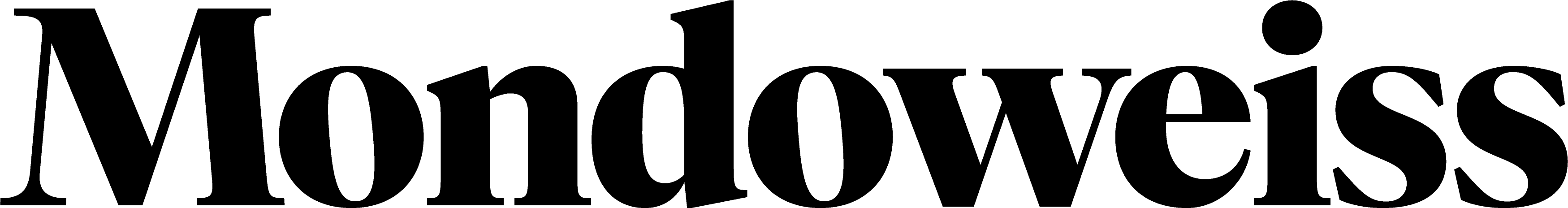当艾玛·特纳尤卡在家乡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开始组织活动、争取平等时,她还是个青少年。仅几年后,21岁的她就带领了12000名山核桃剥壳工(大多为墨西哥裔美国妇女)进行罢工,激情澎湃,也因此最终成为三K党的目标,在激进劳工运动史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
而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受特朗普当局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的挑衅和歧视性指挥,进行了全国范围的名为“追逃”的绑架行动,并自此在圣安东尼奥实行了超过两百起逮捕。此种国家背书的绑架行动和充满仇恨的本土主义的复兴让我们不禁纪念特纳尤卡勇于斗争的精神。
特纳尤卡于1916年在圣安东尼奥出生,当时墨西哥革命风起云涌,震动世界。她的童年经历了大萧条带来的极端贫困,以及因数百万墨西哥人被大规模从美国驱逐至墨西哥(即名为“遣返行动”的时期)造成的影响。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浪潮异常狂热,其中有些特征类比今天,如将外国人描述成煽动叛乱者和社会污染物。
20世纪初圣安东尼奥的极端环境集中于今天称为Market Square的地方,其中也影响了特纳尤卡的父母和祖父母。他们在此地经历了这些世界性的历史事件,在各种意识形态辩论、火热的街头闲谈和激烈讨论中发现了其意义。也正是在这里,年轻的艾玛接触到了那些组织起来的劳工群体,他们参与男女同校教育,透过报纸和集体学习,营造了一种激进氛围。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墨西哥革命者会经常向狂热的人群发表演讲。
特纳尤卡第一次涉足组织政治是在高中,从加入拉丁美洲公民联盟(LULAC)开始。但她没有一直留在那里,原因在于,该组织背离了对宣扬国际主义的承诺,把会员局限在了墨西哥裔美国人,并拒绝墨西哥国民加入。为此,她改换门庭,在1937年即20岁时加入共产党,致力于无国界的工人阶级运动。她随后开始在圣安东尼奥各地发表政治演讲,招来了全市范围内激烈的抹红运动,以年轻的特哈纳族共产主义煽动者身份遭到反对。
而在坚定信念的引导下,她挺身而出,领导了历史性的山核桃剥壳工罢工,即一场由约12000名工人参与的抗争。其中多数是墨西哥裔美国妇女和女孩,她们在闷热的棚子里工作,每磅产品中只赚几美分。这些工人是圣安东尼奥发达的山核桃产业的隐形基石,他们弯腰工作,在灰尘中呼吸,通常每周只能带回家不到一美元。1938年,老板们还试图进一步削减工资,引发了德克萨斯州史上最大罢工。
山核桃剥壳工的不满在特纳尤卡参与运动前就已经存在了,但由于特纳尤卡激进的政治教育和敏锐的战略头脑,她成了该组织最有力的发声者,也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者。罢工持续了三个月,在此期间,特纳尤卡一直居于领导者地位,既在幕后组织工人,又代表工人与公众互动。“我被逮捕了好几次,”她后来说,“但我从来没想过是不是应该恐惧,而是想正义究竟在哪。”
州政府以暴力进行回应,实为我国血泪劳工运动史上之典型,而这种大规模镇压几乎总是给穷人准备的。圣安东尼奥警察局发动的镇压甚为猛烈:他们突袭罢工集会,对和平抗议者使用催泪瓦斯,逮捕了一千多人。特纳尤卡本人也是目标,她被逮捕,并被媒体跟踪。德克萨斯游骑兵队则站在雇主一边,可见在德州,警察和准军事暴力机构会自然联手为资本利益服务。而罢工者自始至终都在坚持抗争。在勇敢面对暴力和饥饿三个月后,罢工者赢得了加薪。
随后同年,特纳尤卡应邀在圣安东尼奥市礼堂发表演讲,讲述她在罢工中的经历。但当地的反动派并没有就此罢休,数千名反共分子冲入礼堂,其中包括数百三K党成员和白人至上帮,他们包围了大楼,阻止她的活动,特纳尤卡不得已从后门逃跑,以防暴徒袭击。
这不仅仅是反动派的报复,而是国家性的针对种族的恐怖行动,意在打击一个女人的生活,使其不得有超越工资谈判而谋求革命的理想。联邦政府已经在关注特纳尤卡了。关于她的FBI文件总累积达181页,这也便是那旨在将劳工激进分子和共产主义者定为“国内威胁”的大计划一部分。
在监视、骚扰和公众排斥下,她被迫离开圣安东尼奥去了旧金山。当她20年后再回来时,发现自己因为与共产党的关系而被禁止参与政治。她开始时难以找到工作,而最终当了学校教师。而在恶意抹红下,她还是没有放弃政治理念。她看到了压迫问题的根源:经济剥削、种族隔离和边境军事化都是相互连结的,且无法假装这种连结是不存在的。无论如何,她的思想都是超前的,其分析仍然适用当今的抗争。20世纪40年代,她加入了对日益强大的边境巡逻队的抗议工作,并与工人联盟组织活动,将争取工作与反对驱逐出境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特纳尤卡在1999年去世后,才重新被公众所熟知。多数时候,对她的新定位是“墨西哥裔美国民权活动家”,以此安全纪念,而她的政治派别和阶级斗争承诺则被忘得一干二净。
那些与现在的相似之处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如今的那些ICE分子没有戴白色头套,但也戴着口罩或以其他方式遮挡自己的身份。他们在阴影下活动,无视各个社区和学校的尊严,受警察局的全力支持,又因市政府无力管制而猖獗,在加油站把父亲带走,无耻追赶那些因恐惧而逃到树上苦苦哀求的人。他们的目的还是老一套:散播恐怖,惩戒已受过度剥削的劳动阶层,强化种族和民族分裂,并提醒有色人种工薪阶级家庭:这个国家的精英可以毫不犹豫地把惩罚官僚机构的暴徒扔到他们面前。
但就像特纳尤卡的时代一样,人们会抵抗。在圣安东尼奥,圣安东尼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协会(DSA)、圣安东尼奥联盟(San Antonio Alliance)和圣安东尼奥立场(SA Stands)等团体正在动员起来,支持无证人士反对ICE的特权。年轻人再次在恶劣的条件下组织起来,系统应对ICE的警报,进行法庭监督,并谴责两党中推动这苦难制造体系的政客。他们选择团结,而非对虚构边界的效忠。他们明确指出了警察行动、边境军事化和资本主义剥削之间的联系,甚至根据特纳尤卡的国际主义精神,将此刻发生的问题与加沙的种族灭绝联系起来。
特纳尤卡的一生提供了比蓝图更有用的东西:一个有深度的道德观明确的例子。她的故事提醒我们,斗争是漫长的,但也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会受到镇压;镇压是不可避免的。如特纳尤卡所言,问题在于我们是否会选择正义而不是恐惧。
Alex Birnel是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社群组织者。